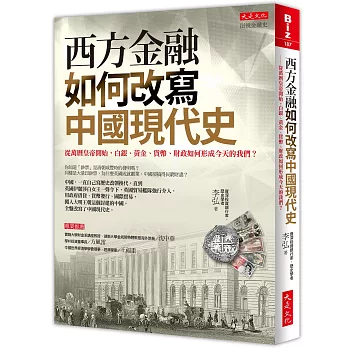本文節錄自《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》的「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?貨幣還沒統一」以及「貨幣崩盤,國民黨丟了大陸」兩節。
本系列前一篇文章講到了宋子文及孔祥熙對「廢兩改元」的貨幣改革貢獻,本篇則將節錄作者對於國民政府如何敗壞財政政策而丟了中國大陸。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小蔣「打老虎」的部份細節。以前在學校時,老師會跟我們說國民黨因為貪汙腐敗而丟了中國大陸;但究竟怎樣的執政者會願意寧願失去政權也要「貪汙腐敗」?卻是學校老師沒辦法再進一步教授的知識。
以下節錄本書幾段文章分享:
1927~1937年的民國,不管是縱向對比通商銀行成立時的清末,還是橫向對比危機與戰爭壟罩下的西方,頗有建立財政金融「新秩序」的希望。這個中國版的新秩序應當包括:中央政府統一稅制幣制、維持穩定以利工商金融業的發展、平衡財政與調整內外債、收回列強控制的海關與國際貿易權。但這只是一個可行的方向。當布列頓森林體系在「二戰」後,奮力搶救全球資本主義之時,國民政府把希望變成了徹底失望。
把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淵的兩隻手,是特權與貪腐。
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,並非是為了高官自肥,而是為了執政黨的一個信仰,即用「三民主義」統一中國的「革命理想」。這一理想驅使著國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,獨攬軍權與政權;統一稅制幣制,行程以「四行二局」為中心的國家金融體系;兼併中國通商、中國實業、四明三個小銀行,實行外匯管制。1930年代這一系列「順應時勢」的金融改革,背後最大的動力之一,就是支持國軍四面征討反動力量,實現當年北伐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主張。
1928年以後的五年中,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了將近四倍,主要靠的是借款。財政支出的50%直接紀錄為軍務支出。這一比例在1936年降為30%,但政府已經債務高企,利息支出上升為收入的45%。等到政府可以玩轉中央、中國兩個銀行,印鈔機就彌補了大部的軍事開支窟窿。民國經濟的發展,不過是國民政府軍事財政的副產品。
抗戰結束的那一年,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金庫裡,已聚積了黃金六百萬兩,可用的外匯資金有八、九億之多,還有大量接收的敵偽資產、各類罰沒、名目眾多的「獻金」,也能折合數億美元。美國人贈送了大量的軍備武器與大筆優惠貸款,列出來是一個長長的單子。恐怕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,財政金融上還沒有過如此揚眉吐氣的日子。中央銀行和美國人給了國民政府新的底氣,蔣介石摩拳擦掌,要重拾「統一」中國的舊業。
可是,此時為國民政府當家的行政院長宋子文,卻心懷忐忑,他對蔣介石此時的政治抱負非但不感興趣,而且相當悲觀。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復國民經濟,拓寬和西方的貿易往來,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援助的實施。同樣心懷忐忑的公眾,只見行政院在蔣介石的默許下,不停的頒布外匯管理辦法與進出口管理的法令、法規,但看不到黃金和美元在銀行間已悄然轉手交易。1947年,蔣介石的國共決戰布局還沒有完成,宋子文控制的財政部、和貝祖貽擔任行長的中央銀行,已經把國民政府的家底暗地裡當掉了一半。中央銀行黃金儲備縮水了60%,物價飆升,引發了金融市場混亂。
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迫於風潮和輿論壓力,監察院曾出重手,也是唯一的一次,彈劾了違法套利的蔣介石的郎舅,和瀆職投機的央行官員。
在大企業和權勢家族大發橫財的同時,末日的國民政府卻財源枯竭,外債無門,內債無路,海外對華投資亦裹足不前。唯一的救命稻草是開足馬力印鈔。法幣和金圓券一前一後,損毀著民國脆弱的貨幣金融肌體。到了1947、1948年,物價的上漲變成了以日計、以時計。赤字和貨幣雲山霧罩,朦朧中財務發生了重大轉移,在美國的銀行裡誕生了一批民國權貴富翁。
1948年8月,蔣介石親自領導一場對通貨膨脹的反擊戰。為此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經濟管制委員會,直接隸屬行政院。而這個委員會的兩員大將,一位是央行總裁俞鴻鈞,另一位就是血氣方剛的蔣經國。這是場雙向出擊的戰鬥,「東線」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銀,稅換法幣,統統改為使用金圓券,並把幣值縮小為三百分之一;「西線」市政府推出的法令,禁止物價與工資上漲、懲罰聚眾鬧事。
改革派的壯舉激情澎湃,結果卻事與願違。蔣經國「打虎」七十天變成了「騎虎難下」。說到底,他的使命不僅是「改革派」與物價、法幣的一場較量,而且是與金融特權和貪腐勢力的一次對博。強制收回民間金銀的法令也成了一紙空文,碰到在海外有一定資產的人,就可以全部豁免,孔宋等大家族的財富得以保全。
OTORI
8/8/2019